南方的春天總是急急忙忙�。三月初,木棉花燒紅了整座城市���,四月風(fēng)起�,金黃櫟鈴木染黃了沿江兩岸。這兩種南方獨(dú)有的花有個(gè)共性�����,開(kāi)花時(shí)見(jiàn)不到一片綠葉,光禿禿的枝干上全是單純的花����,開(kāi)得不管不顧,像要把攢了一年的力氣都用在綻放上���。
對(duì)于一個(gè)北方人來(lái)說(shuō)�,初次見(jiàn)到木棉花就深深留在記憶中了�。坐巴士從家到香港機(jī)場(chǎng)途中的一站,路邊有棵碩大的木棉花�����,樹(shù)枝延伸到地鐵站出口的上蓋屋頂���,花落時(shí)����,整個(gè)頂均勻地撒滿了火紅的木棉花�,像是有人特意布置過(guò)一樣,那一刻總想巴士多停留一會(huì)兒���,也不急著趕飛機(jī)���。此后每次去機(jī)場(chǎng)���,都會(huì)坐在巴士的二層,因?yàn)閺陌褪康亩油^(guò)去�,奪目而炙熱的木棉花讓那個(gè)地鐵站出口充滿了浪漫的詩(shī)意。
聽(tīng)說(shuō)金黃櫟鈴木是南美洲的新移民�����,香港也有不少����,但成片的不多����。而深圳的四月就被那轟轟烈烈的黃色盡染了整個(gè)城市。一樹(shù)金黃�����,燦爛奪目���,沒(méi)有綠葉的陪襯���,只有純粹的金黃讓人陶醉�。不經(jīng)意間覺(jué)得櫟鈴木和深圳人之間有種特別的默契���,它開(kāi)得熱鬧卻走得干脆�����,就像深圳人處理工作的利落勁兒���,該綻放時(shí)全力以赴,該退場(chǎng)時(shí)絕不留戀�。
兩種花的花期都是短暫的,木棉花從綻放到飄絮不過(guò)十馀天�,櫟鈴木的金色浪潮也頂多持續(xù)兩周,這可能也是最動(dòng)人之處�,繁華與凋零皆不拖泥帶水,所有稍縱即逝的美����,都藏著循環(huán)往復(fù)的深厚情感,一座城市的浪漫也是這樣周而復(fù)始,卻始終帶著新鮮感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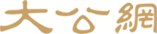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